您现在的位置是: 首页 - 品牌圈 - 贾樟柯监制戛纳获奖片记忆治好了我的电影院睡着羞耻 品牌圈
贾樟柯监制戛纳获奖片记忆治好了我的电影院睡着羞耻
2024-10-29 【品牌圈】 0人已围观
简介也许贾樟柯自己也没有想到,他费力引入的一部获奖电影,最热门的标签竟然是“好睡”。 6月22日,贾樟柯监制、戛纳金棕榈得主阿彼察邦执导、蒂尔达·斯文顿的电影《记忆》终于与内地观众见面。 为何说“终于”,因为此时距离它拿下第74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已经过去了两年多。官宣定档的那天,许多电影博主说:“这竟然是真的。” 监制贾樟柯独自承担了该片在内地的宣传推广任务,但上映三天
也许贾樟柯自己也没有想到,他费力引入的一部获奖电影,最热门的标签竟然是“好睡”。
6月22日,贾樟柯监制、戛纳金棕榈得主阿彼察邦执导、蒂尔达·斯文顿的电影《记忆》终于与内地观众见面。
为何说“终于”,因为此时距离它拿下第74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已经过去了两年多。官宣定档的那天,许多电影博主说:“这竟然是真的。”
监制贾樟柯独自承担了该片在内地的宣传推广任务,但上映三天,《记忆》的票房才刚刚超过90万。
影迷是这部电影的最大受众,但显然,目前它还没有最大程度地触及更广泛的影迷。这使得许多已经观影的影迷开始自发制作梗图,其中“好睡”梗图传播最广,广到贾樟柯都忍不住说“网友们挺皮”。
经过影迷的欢乐操作,这部电影的排片竟奇迹般地从首日的0.2%上升到了0.5%,也算是辛酸之中略有安慰吧。

不必羞耻
POST WAVE FILM
如果你跑了很多影展或在电影资料馆混迹许久,大概率就会对在电影院里睡过去这件事“脱敏”。
因为有时候,你的入睡,就是观看这部电影的其中一环。
有人会拿毕赣的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的观影体验与阿彼察邦的《记忆》相比,但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仍然是一个连贯的绵延的梦,而《记忆》实际上是一个章回体,甚至可以说,它不属于一种既定的、精巧的结构。
与其探讨毕赣是否学习了阿彼察邦,倒不如说,两个人的精神导师同源,那就是侯孝贤、杨德昌和蔡明亮。


老实说,把杨德昌电影放在“好睡”的行列里有些冤枉,他的片子要么如《一一》一样丧又狠,要么像《独立时代》一样俏皮讽刺,前者是砍刀,后者是暗箭,怎么能睡得着呢?
我想,阿彼察邦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导师是侯孝贤和蔡明亮,他俩共同的影像特点就是大量使用固定机位,就拿阿彼察邦最近上映的这部《记忆》来简单地归纳一下,其实就是数个固定机位长镜头拼接起来的。
真的,就是“拼接”这个动词,因为长镜头与长镜头之间都不会有自然的转场。当然,这一点不属于侯孝贤,它确认是来自蔡明亮。

而在镜头的使用习惯上,有一点完全属于阿彼察邦的是,转场附近的镜头很多都是静止的,它会让你突然怀疑自己的眼睛和精神、怀疑影院的放映设备:是我睡过头精神恍惚了还是真的卡了?直到你振作精神,发现画面中有草被风轻轻拂动。
阿彼察邦将这种观影体验形容为“电影引渡我们到梦的世界,苏醒之后,我们仍然在那里,几乎就像一种特别的旅程”。

因此可以说,针对这一类型的电影,观众的入眠,也是观影体验的其中一环。所以,无需为看得奖艺术片入眠这件事而感到羞耻,你成功地get了导演的意图,进入了梦的世界呢。
关于没看懂
POST WAVE FILM
“好睡”对应的另一件事就是“没看懂”,翻看当年戛纳首映映后的影评,会发现有不少人睡了过去,而且醒来之后发现其他人也没看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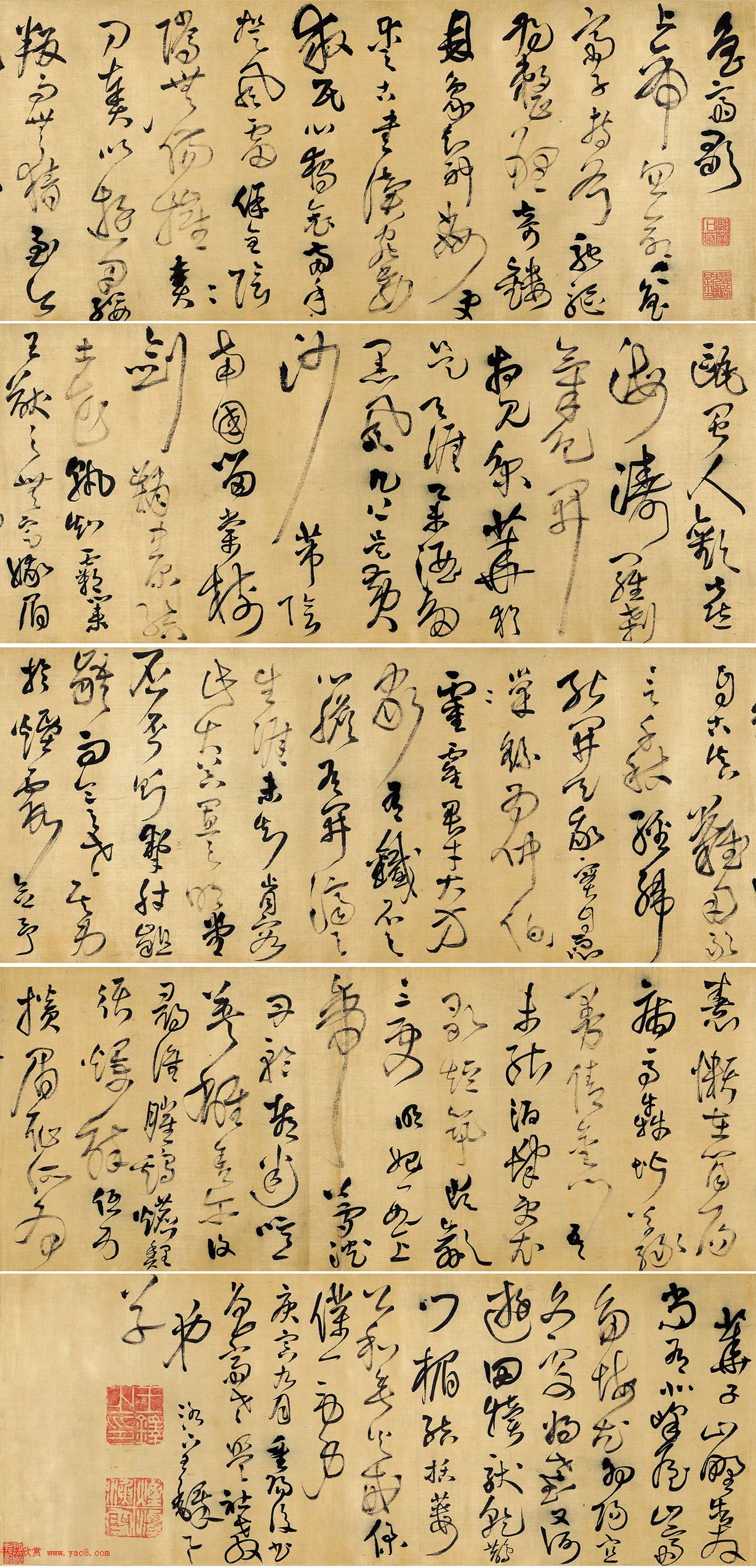
其实这类影片往往都有一个很好懂的梗概,但细节拆分之后,却有太多不确定的具体内容。
《记忆》的剧情,用大白话讲述是这样的:蒂尔达·斯文顿扮演的杰西卡来到哥伦比亚探访自己的姐姐,但她总是会听到奇怪的巨响,于是她就去寻找这种声响的根源。在寻找的过程当中,她经历了一些真实的相遇和虚构的幻想。
所谓的不确定,来自于四点:
一,哪些是真实,哪些是虚构呢?
二,声音指代的是什么?
三,如果是真实的,哪些是属于杰西卡个人的人生记忆,哪些是属于这片陌生土地的历史?
四,如果是真实的记忆和历史,它们处在时间轴上的哪个位置?
比较典型的一场戏,是杰西卡见到了埃尔南。在一开始的场景里,观众并未意识到埃尔南的存在状态,直到在他躺下之后,杰西卡问他对死亡的感受,人们才知道,埃尔南是一个死去的人。

后来两人进入室内,杰西卡才意识到,身处在这个环境之中的人,并不是自己,而是埃尔南,多年之前的埃尔南,她进入了埃尔南之前存在过的一个场景。

这就是艺术电影在视听表达上的特点,因为通俗的电影会直接告诉你这是记忆,比如画面调成黑白,比如打个“二十年前”的字幕,但这种艺术片就会不给你一个确定的时间和场域,逐步释放信息给你,让你自己去探索,自己去解析。
在后面的镜头里,杰西卡握住埃尔南的手,于是两人仿佛接通了蓝牙,此时的杰西卡接收到了一段讯息。
这段讯息是以声音的形式传播的,它有婴儿的啼哭、儿时的对话和男子的呼号,杰西卡时而感到哀伤,时而感到迷惑,时而感受到震撼,有些似乎与她休戚相关,有些似乎是遥远的哭声,前者是个体的记忆,后者是国家的历史。
如果知道了阿彼察邦创作这部电影的背景,大概就能知道这部电影的核心内容。阿彼察邦是在哥伦比亚旅行的时候,听到了一声巨响,于是开始想象和思索,最终创作了这部电影。
其实它就是一个外来者来到一片初次到达的土地、产生的脑内戏剧的体验,这份体验带着个人记忆,又被这片土地的历史所侵入了,混成巨响,在感官里爆炸。
这部电影的视听创新之处,就是没有用画面来展现记忆,而是用声响。
其实也很好理解,因为导演的这种感受是一声巨响引起,而他被调动的记忆是画面不明晰的,他所感受到的这片土地的历史也并不是某种影像,可能是历史的哭声、听说的故事、远处的轰鸣,它们难以名状,最终,通过声音表达了出来。
如果你也感受到了这一点,你就和导演共同站在了哥伦比亚,就好像杰西卡和埃尔南站在了一起。
“有些电影,其实不用‘看懂’。”
——之前,有人在评价《太阳照常升起》时这样说过,也有人在评价《聂隐娘》时说过,后来还有人在评价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这样说过。
大部分时候,这确实不是一种挽尊,因为电影是一种综合的艺术,也就是一种通感的艺术,通过影像和声音的糅合,给你传达了一种更复杂的感觉。
电影市场能有这样一部不一样的电影,很不容易。它值得人们多去感受,把视听的感官撞击得再阔大一些。






